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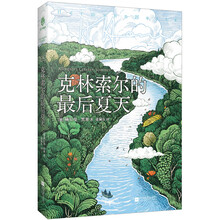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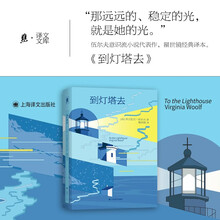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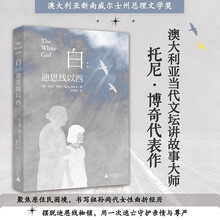
☆ 2014年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明镜周刊》上榜畅销书。
☆ 作者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继《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后,十年磨一剑的重磅之作。
☆ 自由穿行于历史与现实,描绘东德村庄万花筒般的肖像。莱比锡书展大奖评审委员会赞誉“小说以众声合唱的方式讲述村庄自己的故事,是小说写就的赞美诗,令人难以释卷”。
☆ 小说语言和叙事形式的高度革新!幽默与诗意交融,是当之无愧的“小说中的诗歌”。
故事发生在德国东北部勃兰登堡州一个名为菲斯滕费尔德的小村庄,时间集中在"安娜节"前夜的24小时内。
菲斯滕费尔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过东德时代的工农业繁荣,如今却人口缩减,开始衰败。此时,整个村庄陷入夜幕,故事却仍在继续:开渡船的艄公死了;聚集在乌里家车库喝酒的男人们轮流讲故事;90高龄的克朗茨太太,一位患有夜盲症的女画家,用画作记录村里的一个个面孔和村庄的变迁;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正在绕着村子夜跑,撞上了试图自杀的施拉姆先生;一只母狐狸出洞为幼崽觅食……历史上,这里有被指控为女巫、处以极刑的年轻姑娘安娜,也有击退流寇拯救村庄的女勇士安娜。村子几百年间的变迁和传说穿插其间,历史与当下、传说与现实不断闪回交织,萦绕在生生不息的村庄周围,如漫漫长夜中的璀璨星河,拼成了一曲乡村生活的悠远长歌。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莱比锡书展大奖评审委员会
斯坦尼西奇创造出全新的人物形象——集体讲述者“我们”。“我们”是匿名的、敞开式的,是村庄自己的声音,是多声部的存在。它见证了万物变迁,时而百岁高龄,时而又如电视机和本地小报一样鲜活。
——德国《南德意志报》
斯坦尼西奇有舞者般的高超技艺,在不同风格之间自如切换。小说将众多的人物形象编织成多线并进的故事集,甚至包含了动物视角,将传说与记忆、过去和现在统统汇入晚夏之夜的梦中。
——英国《独立报》
斯坦尼西奇这部小说令人情不自禁联想起君特·格拉斯对德国历史的呈现。这部小说或许没有《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式的激情和哀挽,但经过战争和流亡的作者深知,一个安静时代里的安静小镇自有其难以抗拒的魔力。
——英国《独立报》
这部小说有许多奇趣之处:在中世纪历史和现实中自由穿行,对德国的政治现实有敏锐的观察;插曲式的书写手法,古怪的奇思妙想;每当你进入一个角色,他就短暂消失了!
斯坦尼西奇为扑克脸般一本正经、严肃无趣的德国当代小说带来了巴尔干的机趣。
——英国《卫报》
小说为一个德国村庄描绘了一幅万花筒般的肖像,探讨了我们与历史的关系、铭记历史的责任等严肃主题,但这部幽默小说也不会特别沉重,结尾充满救赎意味,又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美国《出版人周刊》
阅读此书令人愉悦,既富有机趣,又极具巧思。
——美国《科克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