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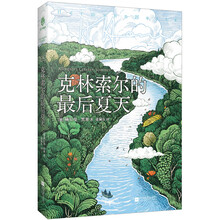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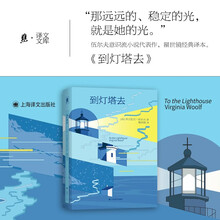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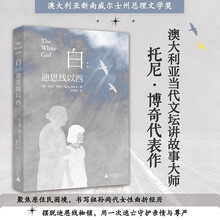

• 《恶童日记》作者雅歌塔流亡记忆的隐秘回响,冷峻精简的语言质感,道尽暗涌的记忆与真实的人生痛感
• 28个虚构故事和1部自传体小说。虚构故事让不堪承受、不能说出的情感得以安放;真实人生的碎片是比故事更残酷的现实,是一切谜题的答案
• “沉闷的工作、沉默的夜晚、被冻结的生活,我不得不把它们都写下来。”
书稿为四本小书的合集,体例与内容各有特色,共同呈现出现实与梦境交织的迷幻风格。和“恶童三部曲”一样萦绕着残酷与幻灭的黑色氛围,但这四部作品的笔触更轻盈多变也更贴近作者本人的声音。
《噩梦》由25个既像梦境又像现实的故事片段构成。部分写真实生活中的荒谬无奈,部分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感。日常生活在雅歌塔的笔下犹如“一种巨大荒谬的呓语所组成的牢房”。写实者如《信箱》,一个孤儿每天查看两次信箱,二十年来一直期待有一天能收到父母的来信,终于有一天他真的收到了父亲的信,而这封信却让他只想逃到一个父亲找不到他的地方。超现实者如《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一个男人一直在废弃的车站等待一辆北上开往家乡的列车,他毒死了不愿让他离开的爱犬并为其雕了石像,最后一次拥抱那只狗的雕像时,男人也变成了“雕像”,永远不再离开。
《昨日》是一部虚实交织的短篇小说。身世坎坷主人公桑多尔在钟表厂里日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生活了无希望。直到一天意外与童年旧友琳娜重逢,他疯狂追求琳娜却毁了琳娜和自己的生活。
《你在哪儿,马蒂亚斯》由一个短篇小说和一部剧本组成,小说部分是一个梦境与现实交融在一起的迷幻故事;剧本部分是一个跨度十年的爱情故事。其中与《昨日》相同的人名和相似的情节使其仿佛是《昨日》的延续或另一种可能。
《不识字的人》是雅歌塔自传性质的小说。11个章节,写了人生中的11个片段。从匈牙利的童年记忆、寄宿学校的生活到瑞士的流亡生涯,刻画出她如何一步步从一个匈牙利乡村女孩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
《噩梦·错误号码》
我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它好像和很多人的号码相似。但这点并不让我感到厌烦,因为每一通电话都是我无聊生活的一次消遣。自从我失业以后,有些时候会觉得有些无聊,只是有些时候,也只是有些无聊。白昼过得实在太快,我有时会想我们之前是如何在那么短的一天里工作满八个小时的。
相反,夜晚总是很长又很安静。正是因为这样,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虽然很多时候,甚至几乎是全部,都是误拨,不过是打错了而已。人们总是那么粗心。
“朗特曼修车厂吗?”电话那头问道。
“不是,谢谢。”我尴尬地说(要改掉这个喜欢说谢谢的习惯),“我很抱歉,您打错了。”
“蠢极了,”电话那头的男子说道,“我的车抛锚了,在塞日耶尔和阿勒斯河之间。”
“很遗憾,”我对他说,“我没法给您修理。”
“这到底是不是朗特曼修车厂?”他开始不耐烦起来。
“很抱歉我这里不是朗特曼修车厂,但也许我可以帮到您……”
我总是在接电话的时候保持友好,即使这其实没什么用。人们从来都不知道,也许我们可以建立联系,成为朋友。
“那好,你带壶油过来就算是帮到我了。”
他的声音中带着点儿希望,觉得是撞到了一个老好人,确实如此。
“我很抱歉,先生,我没有油,我只有一些可供燃烧的酒精。”
“那就烧了它吧,蠢货!”他把电话挂了。
他们总是这样,那些打错电话的人。当你不能达成他们的期望时,总是这样冷漠。我们也许可以聊一聊也说不定。
我还记得最美的那次误会。电话铃响了很久,那时我心情很低落,不愿接电话。对方是个女人,晚上十点打来的。我用透着焦虑与麻木的声音说道:“喂?”
“马塞尔吗?”
“什么?”我小心地答道。
“哦!马塞尔!我找了你好长时间。”
“我也是。”
这是真的,我找了她很久。
“你也是?我也觉得。你还记得吗?那次在湖边。”
“不,我不记得了。”
我这么回答是因为我真的很诚实,我不想说谎。
“你不记得了?你当时喝醉了吗?”
“有可能,我经常醉酒。但我不是马塞尔。”
“当然,”她答道,“我也不叫弗洛朗斯。”
哦,起码知道她不叫什么了。我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她突然又说道:“确实,您不是马塞尔,但是您的声音很好听。”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但她继续说道:“一个非常舒服、深邃、温柔的声音。我希望能认识您,见您一面。”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您还在吗?为什么您不说话了?我知道是我打错了,您不是马塞尔。我想说的是,您不是那个之前告诉我他叫马塞尔的人。”
又是一阵沉默。
“您在听吗?您叫什么?我叫加朗斯。”
“不是弗洛朗斯?”我问她。
“不,我叫加朗斯。您呢?”
“我?吕西安。”(这不是真名,但我觉得加朗斯也不是。)
“吕西安?真好听。我们要不要见一面?”
我什么也没说。汗水从前额流到眼皮下。
“这肯定很有趣,”加朗斯说道,“您不觉得吗?”
“我不知道。”
“我希望您还没结婚?”
“不,结婚,不不。”(我结婚了?这是什么想法!)
“那么?”
“好的。”我回答。
“好什么?”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见一面吧。”
她笑了笑:“您是个害羞的人,我觉得。我喜欢害羞的人。(马塞尔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听着,我来想想。我明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会去剧院咖啡馆。明天,周六,我想您不工作吧。”
她说得对。我周六不工作,别的日子也不工作。
“我会穿着……”她继续说道,“我想想看,一条苏格兰短
裙,灰色的衬衫和一件黑色的马甲。很容易就可以认出来的。我
的头发是棕色的,中等长度。等等……(我一直在等着。)我会
在桌子上摆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您呢?”
“我?”
“是的,我怎么认出您呢?您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我?就像您喜欢的那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您有胡子吗?络腮胡?”
“不,没有。我每天早上都会简单地刮一下。”(事实是每三天或者四天,这得看情况。)
“您穿牛仔裤吗?”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但她肯定喜欢这样的打扮。)
“还有一件宽松的黑色套头衫,我想。”
“是的,黑色的,几乎都是黑色的。”我这么回答她肯定很高兴。
“哦,”她说,“短发?”
“是短发,但也不是很短。”
“您是金发还是棕发?”
她令我不爽,因为我的头发是脏脏的棕灰色,但是我不能这么说。
“栗色的。”我对她喊道。
如果这让她不高兴的话,那跟我对她说实话也没什么差别。现在想来,我更喜欢那个车子抛锚的小子。
“这有点不太好认,”她说,“不过我会认出您来的,您到时候夹着一份报纸如何?”
“什么报纸?”(她真是过分,我从来不读报。)
“《新观察者》如何?”
“好的,我会带着一份《新观察者》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报纸,不过我肯定会找到一份的。)
“好的,那明天见了,吕西安。”她说。在挂断电话之前,她还补充道:“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极了!有些人总能轻易地这样说,而我从来都说不出来。有一堆词我都无法说出口,比如“有意思”“令人激动”“充满诗意”“灵魂”“痛苦”“孤独”等等。非常简单,我就是说不出口。我很惭愧,就好像这些词和脏话一样很下流,就像是“我操”“他妈的”“我呸”“贱人”等等。
第二天上午,我去买了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黑色套头衫。售货员说我穿得很好看。但是我总觉得非常不习惯。我还去了趟理发店,理发师向我推荐了一款染发膏,我就让他做了,深栗色,管他呢,要是失败了我就不去了。最终染得很好。现在我有一头漂亮的栗色短发,只是我依然很不习惯这样。
我回到了家,看着镜中的自己,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那个陌生的人,也在看着我。我非常不爽,他比我好看,比我年轻,可他不是我。我没他那么好,我不漂亮、不年轻,可我习惯了。
现在四点差十分,必须要出发了。我迅速开始换衣服,我又穿回了原来的那套褐色灯芯绒衣服。我也没买《旧观察者》。四点一刻的时候,我到了咖啡馆。
我坐了下来,开始四处观望。服务生来了,我点了一小杯红酒。继续四处张望着,我看见四个正在玩牌的男子,一对视线放空、百无聊赖的情侣。另一张桌上,我看见了一位穿着灰色百褶裙,浅灰色衬衫和黑色马甲的女子。她还戴了一条三串银链子相扣的长项链。(她没和我说她会戴项链。)她面前,有一杯咖啡以及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因为距离比较远,无法看出她的年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很漂亮,非常漂亮,对我来说太漂亮了。
我还看到她有双悲伤的美丽的眼睛,眼底带着某种寂寞。我想去赴约,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穿的是我之前那套灯芯绒的衣服。我去了趟厕所,朝镜中的自己瞥了一眼,我的栗色头发让自己觉得不知所措。我同样也为想要去赴约的冲动而感到羞耻,去走向“那双悲伤的美丽的眼睛,眼底带着某种寂寞”,这不过是我愚蠢而任性的想象罢了。
我又回到大厅里,我坐到一个离她很近的座位上,好好地看着她。
她没有看到我,她在等着一位夹着报纸,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黑套头衫的年轻男子。
她望了望咖啡馆里的时钟。
我一直紧紧地盯着她,这可能惹恼了她,因为她叫来了服务生准备付钱。
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像美国西部片里那样。一个年轻的男子—比我要年轻—走了进来并在弗洛朗斯–加朗斯的桌子前停下。他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的套头衫,我几乎有些吃惊他怎么没配手枪和马刺。他还留着齐肩的黑发,漂亮的黑色络腮胡。
他看了看四周的人,包括我,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说了什么。
她叫道:“马塞尔!”
他回答说:“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是记错了一个数字。”
“你在等人吗?”
“不,没有。”
然而我却在那里,她刚刚就是在等我,但是幸运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也不可能去告诉他们。
尤其是当马塞尔说道:“那么,我们走吧?”
“好的。”
她起身,他们离开了。
……
译者序
噩梦
昨日
你在哪儿,马蒂亚斯?
不识字的人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雅歌塔的小说语言非常冷峻,好像尽量没有什么形容词,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辞藻,尽量都是名词、动词。但是就算只是这么简单,甚至荒唐的一种语言,都让人读得毛骨悚然,完全能够抓住人。——梁文道
我向来喜欢简单的叙述、朴素甚至干枯的语言。因此像海明威、卡夫卡、鲁尔弗、昆德拉、库切、奈保尔(《米格尔大街》)以及村上春树(部分)、青山七惠是我的*爱,现在又有了这个雅歌塔·克里斯多夫。——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