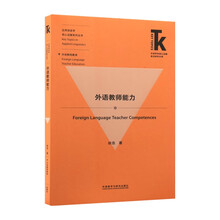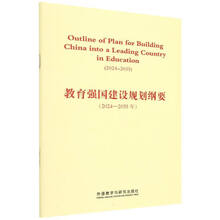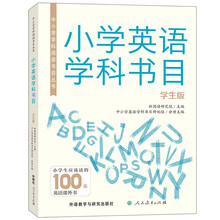导言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通过各种感官的综合运用,感受和认知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感觉的失衡或残缺就像关闭了一扇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窗户,必然造成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模糊或残缺。具有感官功能障碍的人所认知的世界往往是不完整的,大家熟悉的“盲人摸象”故事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领,是人类认知世界、赋予世界意义的方式。在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祖先能够从猿类中脱颖而出,完成向人类的演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所独有的两个文化中的关键特性: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讲故事。这两种特性都要求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邓巴 2016:20)。讲故事的传统不仅贯穿远古时空,照亮了人类演化的进程,更照亮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轨迹。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将人类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认为“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也像是在讲故事”(Sartre2007:12)。可见,叙事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而虚构叙事更是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叙事才能发挥到极致,建构出异彩纷呈的虚构世界,这种精神世界使人类获得了诗意的栖居之所。从可能世界叙事理论来看叙事是对现实世界的表征与模拟,作者在叙事文本中建构的虚构世界就是一个个可能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必定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各种感知和体悟化入叙事文本的虚构世界之中。莫言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过,作家写小说就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应该把他的全部感官调动起来。他讲到自己在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写人身体的感觉,写肉体的、写感官的感觉比较多。他描写一个事物的时候必然要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让文字传递出声音、气味、画面、温度。好的小说应该像充满了人气的街道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气味,有不同的温度,应该让人仿佛置身其中。作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全部感官调动起来那么势必会把小说写得枯燥无味。莫言关于小说创作的这番话表明,作家在创作时必然要充分调动他的全部感官,而虚构叙事中的世界也必然充满了画面、声音气味,并且有温度。因此,虚构叙事中的世界不仅有图像风景(landscape)这个维度,还有声音景观(soundscape)等多个感官维度。那么,何谓“声音景观”?研究虚构叙事中的声音景观有何意义?要探寻它们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讲故事的奥秘”(傅修延1993),就要借助听觉叙事理论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听觉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感官之一,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必然进入叙事的范畴,因此对听觉叙事的研究也成为叙事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听觉叙事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叙事中与声音有关联的部分,它们建构了叙事中的声音景观。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叙事研究几乎都处于“失聪”“聋聩”的状态:与视觉感官有关的研究蔚然成风,“图像叙事”(graphic narrative)、“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叙述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聚焦”(focalization)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而听觉叙事(auditory narrative)研究却在灼灼的视觉聚焦下成为“盲点”,在叙事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声音,反映出学界同仁对听觉叙事的忽视。
究其原因,主要与“视觉为王”的时代特点有关。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最主要的认知方式是靠眼睛读取文字、图片影像、图表等符号系统获取信息,这样的认知方式自然使人类倚重视觉,因而叙事中事件所构成的图景成为叙事研究的首要对象。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视野回溯人类的叙事进程,可以发现媒介的变化影响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叙事的通俗说法就是“讲故事”,“讲”与“听”原本是参与叙事交流且同时在场的两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长时段讲故事的源头时,会看到口头叙事为我们呈现了“讲”与“听”同在的叙事模式。我国历史上的说书人,如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等,都是“现场”讲故事的高手。然而文字,尤其是印刷文字出现之后,原本“讲”与“听”同时在场的叙述方式逐渐改变为不同时空范围中以叙事文本为媒介的“先写后看”的叙事交流方式。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刷屏时代”,导致“‘听’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然是一种可以被忽略甚至是可以被替代的信息接收方式”(傅修延2015b:117)。“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倚重视觉的认知思维。媒介即信息,不同的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不同,应用不同的媒介会造成人类心灵认知的差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论述人类媒介史时,划分了以口头语言、文字与印刷术,以及电子媒介为代表的三个不同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的人类认知思维模式大不相同,社会形态与心理逻辑也不相像(麦克鲁汉2008;McLuhan 1962)。麦克卢汉不仅是电子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而且是大众文化的先知先觉者。他把媒介比喻为暴君,警示世人被媒介奴役的危险境地,并且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断定,社会习俗不是由教育或宗教决定的,而是由大众媒介决定的(麦克卢汉2004)。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应该对麦克卢汉半个世纪前做出的论断颇为惊叹和深有感触,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据《大众日报》此前报道,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互新趋势报告》显示,自2016年以来,我国电视开机率由70%断崖式地下降到2022年的不到30%。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在大年三十看春节联欢晚会,而是选择玩智能手机里的电子游戏或看小视频。电子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沦为了电子媒介的奴隶呢?J.C.卡罗瑟斯(J.C.Carothers在论述文字如何让社会改变想法时指出,“书写文字(尤其是印刷文字)出现之后,改变才准备就绪,语词才开始丧失魔力和能动力……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大致生活在声音世界里,不像西方的欧洲人基本上活在视觉世界里”(Carothers 1959:310)。科技的发展会改变媒介的形式,使人类对不同媒介的倚重不同,“无论是源自某个文化之内或之外,只要对人类某一感官产生压力或优势,所有感官间的轻重比例就会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