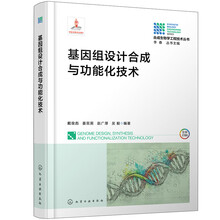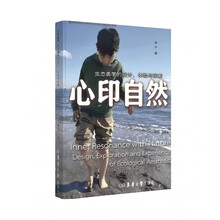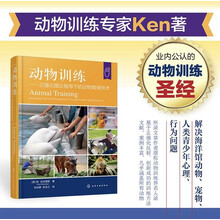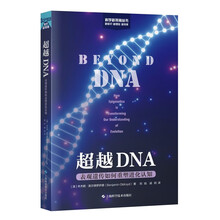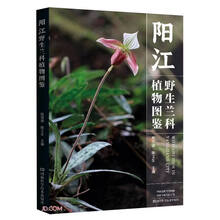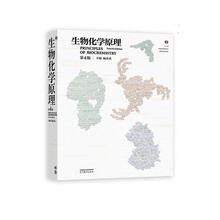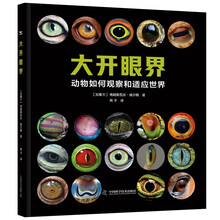总论
石松类(lycophytes)和蕨类(fems)植物,常统称为蕨类植物(pteridophyte),又称
羊齿植物。石松类和蕨类是通过孢子繁殖的维管植物,它们具有相互*立生活的孢子体和配子体,其生活史为孢子体发达的异形世代交替。孢子体有根、茎、叶的分化,有较原始的维管组织。配子体微小,绿色自养或与真菌共生,大部分土生或附生,具假根。有性生殖器官为精子器和颈卵器,生殖行为需借助水进行。据现有研究统计,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有12,000多种,但实际种数可能远不止于此。它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各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种类*为繁多。在生态习性上,大多数蕨类植物为土生、石生或附生,少数为湿生或水生,喜阴湿温暖环境。
一、蕨类和石松类的全基因组研究
2000年,**个完成基因组测序的植物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测序结果公布,标志着植物基因组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近年来,植物基因组测序速度发展迅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基因组被测序。然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因其基因组较大、重复序列比例高、遗传背景复杂、多倍化和杂交普遍,给基因组测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蕨类植物体细胞的染色体2n可高达1260,基因组*大可达1C(148Gb),这比拟南芥基因组大1000多倍。截至目前,已经有10余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完成了全基因组测序,其中石松类植物先后有江南孔氏卷柏Kungi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Banks et al.,2011)、鳞叶卷柏Lepidoselaginella lepidophylla(VanBuren et al.,2018)、卷柏Pulviniella tamariscina(Xu et al.,2018a)、东北石松Lycopodiumclavatum(Yu et al.,2023)和台湾水韭IsoStes taiwanensis(Wickell et al.,2021)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而蕨类植物先后有细叶满江红AzoUa fiftcutodes、勺叶槐叶蘋50lvn.acucullata(Li et al.,2018)、桫沙椤Alsophila spinulosa(Huang et al.,2022)、铁线蕨Adiantum capillus-veneris(Fang et al.,2022)及美洲水蕨Ceratopteris richardii(Marchant et al.,2022)的基因组被报道。*后3种均已达到染色体水平,相信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基因组被揭示。
二、蕨类和石松类的叶绿体基因组系统学研究
与真核生物的细胞核、线粒体相比,叶绿体基因组相对较小,结构和序列保守,且细胞内存在多个拷贝(Mower and Vickrey,2018)。通过比较植物线粒体DNA(mtDNA)、叶绿体DNA(cpDNA)和细胞核DNA(nDNA)的核酸替换率,发现cpDNA的核酸替换
率适中(Wolfe et al.,1987),而且叶绿体基因组编码区和非编码区的分子进化速率存在显著差异,能够为不同分类阶元的系统发育研究提供多样化的遗传变异信息(Clegg et al.,1994),这使得叶绿体基因组在植物系统发育中备受青睐。1998年,Wakasugi等(1998)正式发表了**个蕨类植物——松叶蕨Psilotum nudum的叶绿体基因组。随后,Wolf等(2005)发表了**个石松类植物——亮叶石杉Huperzia lucidula的叶绿体基因组。由于测序物种数量有限,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石松类植物和蕨类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的结构特征和差异上(Wolf et al.,2005,2011;Roper et al.,2007;Tsuji et al.,2007;Smith,2009;Gao et al.,2009,2010,2011,2013;Karol et al.,2010;Grewe et al.,2013;Kim et al.,2014;Zhong et al.,2014)。
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和测序成本的降低,大量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叶绿体基因组被测序。截止目前,叶绿体基因组已测序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有600多种。在石松类植物中,卷柏科植物因其叶绿体基因组具有特殊的正向重复结构而被广泛关注(Mower et al.,2019;Zhang et al.,2019a,2019b,2020a;Kang et al.,2020;Xiang et al.,2022;Zhou et al.,2022)。Kuo等(2018)和Du等(2022)对蕨类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结构变化和基因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此外,叶绿体基因组数据在解析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关键科、属的系统位置、复杂类群的系统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石松类植物中的明星植物------蛇足石杉Huperziaserrata,因其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中*特的药用价值而广受关注,但是通过叶绿体基因组测序和系统发育分析,明确该种实际应为两个种,即分布于我国南方的长柄石杉H.javanica和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H.serrata(Guo et al.,2016;Zhang et al.,2017a)。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叶绿体基因组测序为系统发育研究奠定了基础。Pereira等(2021)和Zhou等(2023a)分别基于叶绿体基因组对水韭科和卷柏科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Lu等(2015)*次通过整合叶绿体基因组数据,构建了蕨类植物在目等级的系统发育关系。Wei等(2017)利用40个叶绿体基因组数据重建了eupolypods II的系统发育关系,澄清了轴果蕨科的系统位置和蹄盖蕨科的单系性。Kuo等(2018)通过扩大取样,对蕨类植物的11个目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发现基于不同的叶绿体基因组数据集确定的膜蕨目Hymenophyllales的系统位置并不稳定。Wei等(2021a)对蕨类植物中附生种类*多的科——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的70个样本进行叶绿体基因组测序,确定了PPGI中系统位置未定的合环蕨属Synammia的系统位置,并结合核糖体数据和形态数据重新探讨了水龙骨科的系统发育关系,提出了水龙骨科下新的亚科分类系统(Wei and Zhang,2022)。
Du等(2021)通过对蕨类植物28个科的208种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取样测序,重新构建了水龙骨目Polypodiales在科等级的系统发育关系,并对蕨类植物早期演化历史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水龙骨目与同期的被子植物有相似的物种分化模式。此外,Lehtonen等(2020)对合囊蕨科Marattiaceae的6个属进行系统发育重建,提出多孔蕨属Danaea应为合囊蕨科的*早分支,而天星蕨属Christensenia则与唇囊蕨属Marattia构成姐妹群关系。Ke等(2022)通过研究叶绿体基因组数据发现,现存的莎草蕨科Schizaeaceae包括小莎蕨属Microschzaea、莎草蕨属Jctoostachys、枝莎蕨属Schizaea和Schizaea
pusilla4个分支,并认为莎草蕨科下应包括至少3个*立属。
三、蕨类和石松类的核基因系统学研究
核基因的双亲遗传特性为揭示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提供了更充足的证据,尤其对研究广泛杂交的蕨类植物类群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在种子植物中通用的核基因片段ITS片段在部分石松类(如卷柏科)中比较容易扩增,但在蕨类植物中却极为困难,这导致基于核基因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子系统学研究相较于种子植物严重滞后。在高通量测序技术发展之前,研究者大多通过一代测序技术扩增核基因片段。在蕨类中,常用的核基因有LEAFY、SQD1、pgiC、gapCP、18S等,但由于蕨类植物杂交现象普遍,核基因扩增困难,获得的数据质量不高且数量极少。因此,大部分核基因扩增主要是用于探究一些复杂小类群的杂交和系统发育研究。Rothfels等(2013a,2015)基于20个和25个低拷贝核基因对整个蕨类系统进行了系统发育研究,构建了蕨类植物系统发育关系,但涉及的物种相对较少。
随着分子测序技术的发展,通过转录组测序、目标富集测序和简化基因组测序方法,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核基因数据,进而开展类群的系统发育研究。例如,Shen等(2018)、Qi等(2018)和千种植物转录组计划(One Thousand Plant Transcriptomes Initiative,2019)先后分别利用68个、119个和70个蕨类植物的大量核基因数据,重新构建了世界蕨类植物的系统发育框架。Pelosi等(2022)整合上述三篇文章的所有蕨类植物共计258个样本的转录组数据,重建了整个蕨类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发现蕨类植物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27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除对蕨类植物科等级以上系统发育的研究,转录组测序数据也常被用于解决科下类群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如水韭科(Wood et al.,2020)、桫椤科(肖永,2019;Dong et al.,2019)、碗蕨科(刘莉,2018)等。Fawcett等(2021)和Lima等(2023)先后通过GoFlag探针的目标富集测序方法分别获取了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和里白科Gleicheniaceae的核基因数据,并重建了这些复杂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
上述这些研究极大地帮助我们阐明了整个蕨类植物的进化关系。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推进,我们将对世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演化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四、PPG I系统之后的蕨类分子系统学及分类学研究
PPGI(Pteridophyte PhylogenyGroupI)是广义蕨类植物分类系统(PPGI,2016),
为世界蕨类植物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且*新的蕨类研究指南,该分类系统的提出对蕨类和石松类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PPGI系统(2016)与秦仁昌系统(1978)(图I),以及Smith等(2006a)、Christenhusz等(2011)以及Christenhusz和Chase(2014)的分类系统存在显著差异。
PPGI系统是由来自全球68个单位94名分类学家联合署名发表的。PPGI系统将世界现存的12,000多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划分成2纲14目51科337属。自发表以来,PPGI系统被全球植物学科研工作者广泛采纳和使用。至今,大量新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极大地推动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研究。世界石松类和蕨类分子系统学与分类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图IPGGI系统(2016)与秦仁昌系统(1978)
1.科、亚科下的属间系统发育关系愈加清晰
在2016年PPGI系统发表之后,近年来通过更深入、系统且全面地取样研究,结合一代和(或)二代测序数据,一些复杂石松类和蕨类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基于此,科下分类系统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例如,石松科(Zhang and Zhou,2021;Chen et al.,2022)、卷柏科(Zhou and Zhang,2023)、瓶尔小草科(Zhang and Zhang,2022)、水龙骨科(Wei et al.,2021a;Wei and Zhang,2022)、禾叶蕨亚科(Zhou et al.,2023)、莎草蕨科(Ke et al.,2022)、桫椤科(Dong and Zuo,2018)、岩蕨科(Lu et al.,2019a)、乌毛蕨科(DeGasper et al.,2017)、蹄盖蕨科(Moran et al.,2019)、金星蕨科(
展开